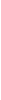恰空Chaconne14
(daowendesile)
我放下琴弓,揉了揉酸胀的手腕。
视线不自觉落在手指上那一圈细细的戒指上。
金属在灯下泛着温润的光泽。当初试戴时的尺寸还正好,如今却隐隐的发紧,指根处都被勒出了一道浅浅的痕迹。
我应该没有发胖才对。毕竟在这些日子里,我几乎没怎么好好吃过饭。
所以,让我变得浮肿的罪魁祸首,大概只剩下酒精了。
可我离不开它。作为我生活中少有的慰籍,哪怕它把我的胃里烧得生疼,我还是需要那种短暂的麻痹感。
就像我离不开她一样。
我原谅她了。
可我心里很清楚——出轨这种事,只要有了第一次,就会有无数次。尤其是 Maggie 这种人,她不可能不去玩。
所以,当又一次回到宿舍发现她不在时,我的心里竟然没有什么波澜;这距离她带我去买对戒、郑重其事地许诺未来,也不过才两个星期。
无所谓了。
我从床下摸出一瓶酒,给自己倒了一杯,又取出一片止痛药。最近我几乎每天都需要吃下它,才能让自己免于疼痛的煎熬,勉强睡着。
我拨开一片药丸,刚抿了一口酒——
“这样对身体很不好的。”
声音在对面床上传来。
我回过头,Abela 坐在那里,一脸担忧地看着我。
“那个止痛药、最好不要和酒精一起吃……”她补了一句。
我眯了眯眼睛,突然意识到自己这段时间总是忽略掉她的存在。
不过她在宿舍的时间也不算多,即便在,她也一直很安静。
她和她姐姐的交流只限于必要的话;而大多数时候,只是窝在床角看书或者对着电脑,戴着头罩式耳机,把自己与外界隔开。
就像许念初一样。
我重新转过身去,把药片握在掌心。
可下一秒,手腕却被她轻轻握住。
“这样对身体不好。”
她看着我的眼睛,语气放慢,一字一句又说了一遍。
她是以为我听不懂吗?
我眨了眨眼,心里莫名觉得好笑——难道在她印象里,我的英语就这么差?
难道这么不了解我吗。我们虽然算不上很熟,却也一起住了这么久。
而且,我们其实偶尔会聊天。
我知道,她对我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在意。大概也是拜荷尔蒙所赐,毕竟我们在亲热时,从来都没有避讳过她。
她会刻意来问我一些大提琴的问题,在我产生疑问时,她又笑着说,因为感觉弦乐之间是相通的嘛。
倒也不算错。
我并不讨厌和她聊天。
不如说是很奇怪的,明明隔着一层语言的壁垒,我却很喜欢向她说很多自己的事情;因为她是会认真倾听的人。
我跟她提到老师的苛刻,是和国内截然不同的严格。我用蹩脚的英语告诉她我比赛选曲中的纠结,谈论我喜欢的作曲家,也讲练习时的瓶颈,还有手臂和肩膀始终消不掉的酸痛。
当我说起以前在国内做过针灸的事情,她瞪大了眼睛,惊讶又好奇。她问我,人类是怎么发现发现扎针可以治病的呢?我说,我也不知道。她说,她也想试试那是什么感觉。我摇头,说还是别了,很痛。
真的很疼的。
隔天,她给我带来一盒膏药。不得不说,效果确实比我之前用的都好。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。
我看着掌心里的止痛药,又抬起头,怔怔地望着她。
深蓝色的瞳孔在灯光下显得干净而清透。她脸上有着细碎的雀斑,与她姐姐如出一辙的褐色小卷发被乖乖束在脑后。
她其实长得很可爱。
我站在原地,没有说话。
不知道过了多久,她小心地拧开一瓶矿泉水,递到我手里,又递来一张纸巾。
“你哭了。”
她说。
后来,我没有喝酒,也没有吞下那片止痛药。
我只是控制不住地抽噎着,小声问她——可不可以抱我一下。
她没有拒绝。
少女的怀抱柔软而温暖,带着干净的味道,我把头歪在她的颈窝。
恰到好处的熟悉感觉,才让我发现,原来她和她一样高啊。
“我可以亲你吗?”
不知餍足的人,总会得寸进尺。
这一次,她依旧没有拒绝。
起初只是一个轻轻的吻,浅浅地落在嘴唇上。可呼吸交缠之后,一切开始慢慢失去控制。
她捧着我的脸,认真地吻着我。可就算她已经很小心,她嘴里牙套锋利的触感还是划到了我的唇瓣。
唔……
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
是久违的,被我遗忘的熟悉的感觉。
许念初在上初中的时,也戴上了这样的牙套。
那段时间我总是暗自苦恼。她接吻时笨拙又急切,总会不小心把我弄疼,可我又舍不得拒绝她难得的靠近。
可在尖利的痛感传来时,我还是下意识推开了她。
她愣愣地跪在床上,耷拉着两只湿漉漉的狗狗眼睛,一动不动地看着我。
“……是我做得不好吗?”
我的呼吸开始加快。
她第一次这样主动地向我靠近。
“不、不是……”我慌乱地解释,“只是刮的我有点疼。”
“那我们再来一次嘛。”她急切地凑过来,“再给我一次机会,好不好……”
我没有再推开她。
即使那一次,她还是不小心弄疼了我。
年少的人啊,总是轻易就被点燃。
呼吸交错,情绪失控。热烈的纠缠之间,异国的少女在一片凌乱中,狼狈地从床上爬起来。卷发早已散落在肩头,修长的手指拉开抽屉,在里面翻出一只避孕套,套在已经硬到青筋遍布的腺体上。
我熟练的帮她撸动着,看她粉红色渐渐爬上她的脸颊。
“我姐姐今晚不会回来了。”
她小心地搂着我的背,温热吐息打在我的脖颈间。
“我知道。”我轻轻地喘息着,我知道是谁。
“对不起。”她说,“她对你不好。”
我知道。我没有再把话说出口,只是默默的闭上了眼睛。
快感很快将一切都淹没。
再一次见到Maggie时,已经是第二天了。上课前一分钟,她抱着书,一个人坐到我身旁。
我跟她打了个招呼,又埋下头去看今天要讨论的文章。打印在 A4 纸上的英文字母密密麻麻,一行挨着一行。
好在,如今我已经能读懂大半,不再像刚来时那样让人头疼。
说起来,我们离开家,也已经快半年了啊。
Maggie 坐在我旁边,心不在焉地扣着手指。她的视线正落在我身上,我能感觉到。我知道她在等——等我像第一次那样失控地质问她,问她昨晚去了哪里,和谁在一起,为什么一整夜都没有回来。
可我没有。
我只是翻动纸页,假装什么都没发生。
我依然是她的女朋友。我依然爱她。就像她说她爱我那样。
虽然,我也有不想被她知道的秘密。
她仍然带我去看她的比赛,在队友面前毫不避讳地吻我。所有人都知道我是她的女朋友。她的社交软件里也只有我。
至于她的朋友们知不知道她在外面乱玩,我不确定。但可以肯定的是,我这种纵容的沉默,让她越来越肆无忌惮。
后来,她开始带我去她们圈子里的派对。
我在那些如梦似幻的夜晚里,接触到了很多人——几乎都是光鲜亮丽、家境优渥的女孩。她们的生活有无数种可能,学习只是其中最无关紧要的一项。成绩不重要,方向也不重要,家里永远有人替她们兜底,让她们一次又一次地试错。
她们的人生没有必须完成的目标。
过剩的精力无处安放——而过早见识过这个世界绚烂一面的她们,已经很难再从普通的事情里获得快乐。
于是,她们选择更热烈的方式去感受存在。
高中女生们,学着大人的样子推杯换盏,玩着无聊的酒桌游戏。暧昧而昏暗的灯光下,笑声、尖叫声、玻璃杯碰撞的脆响混和在一起,空气里全是香水、酒精和体温蒸腾后的浓郁味道。
在这里,没人把自己的感情当回事。你可以喜欢很多人,可以在同一个夜晚与不同的人接吻,可以把暧昧当成游戏,把亲密当成筹码。
只要玩得开心就好。
在这里,我跟着一个前辈学会了抽烟。
她叫什么来着?Amy,还是 Emmy?我已经记不清了。反正都差不多。
那天我们都醉得彻底。余光里,我看到 Maggie 在角落里和一个女孩接吻,灯影晃动,她的手搭在对方后颈,又渐渐往下。
于是,我转过身,靠在坐在身旁的前辈身上,抱住她,然后、主动吻了上去。
她刚抽过烟,嘴里是爆珠的甜腻香精味,混着烟草苦涩的臭味。
在过去的人生中,我一直都很讨厌烟味。
它们会附着在衣服、头发、皮肤上,根本挥之不去。就算丢进洗衣机里反复清洗,也还会若有若无地残留着。
折磨人。
而且妈妈总说,碰这些东西的,都是不叁不四的人。
但那天晚上,却莫名其妙的让我心动。
我从前辈那里讨来一支烟,笨拙地夹在指缝里。她拿出打火机,“啪”的一声,火苗猛地窜出来,我下意识一缩手。
细细的香烟掉在地上。
“你害怕吗?”她笑着弯腰捡起,熟练地点燃,深吸一口,然后缓缓开口,白色的烟雾从她的唇齿之间逃了出来。
“张嘴。”
我听话地照做。
她俯身吻上来,这次是更加直接又浓烈的尼古丁的味道,侵入我的口腔和喉咙。
“咳——咳咳——”
我弯下腰,狼狈地咳嗽,眼泪都被呛出来。
“诶呀?对不起。”她笑着拍我的背,“但这还只是一点点哟。”
好呛。
我盯着她指间那一点猩红的火光,烟头在昏暗里一明一灭。
不舒服的感觉。可我还是想试试。
最后,我只用了一晚上就学会了;并且,对它产生了依赖。
尼古丁带来的那种松弛感,强行让紧绷的神经塌陷,仿佛有人强行把我的身体按进舒适的温床。
不过那天晚上,我也确实和前辈共度了春宵。
她的床品说不上好,但也要比最差的那位温柔了不少
我晕晕乎乎的享受着她在我身后的顶弄。后来又不知道谁发现了在房间里的我们,强行托起我的下巴,和我接吻;又把她的腺体粗暴的塞入我的嘴巴里,一直顶到喉咙的最深处。
前辈似乎很大方的接受了这种行为,和别人愉快的共同享受起这个已经烂醉的Omega来。
不如说,她应该很喜欢这种多人行为;在我身后的腺体更加卖力地抽插起来。
太多刺激了,我想要一些喘息。
可是面前的Alpha根本不给我任何机会。她粗暴地拽住我的头发,强行让我把她的腺体越含越深。断断续续的窒息感让我的眼前一片模糊,身下的快感也被无限放大。
不得不说,我其实很喜欢这样。
不过我大概看起来很狼狈吧,衣服被褪去了大半,两个乳房就这样袒露在空气中,随着动作摇晃着。
简直像一件专供Alpha的发泄玩具一样。
意识浮浮沉沉。这是哪里?只留下远处的一盏小灯,让我看不清任何东西。我独自一人狼狈地蜷缩在床上,脸上、身上似乎都还沾着别人污秽的液体。
门虚掩着,外面的音乐声隔着墙传进来,低沉而模糊,像从水底传来的响动。
我有一瞬间恍惚——
如果被她看到我这个样子,她会生气吗?
这个念头在脑海里转了一圈,沉下去;又浮上来。
如果被她看到我这个样子,她会生气吗?
还是……她根本不会在意。
视线失焦,我盯着天花板上旋转的光影。身体和灵魂像被拆开来,各自漂浮着。我忽然生出一种荒谬的感觉——仿佛自己是一件已经死去、但仍然残留一点温度的物件。
啊,就这样让我死去吧。
像一只被拆坏的旧玩具,被开膛破肚,里面填充的棉絮散落一地。没有谁会认真去修补,也没有谁会为它的破损感到惋惜。
我是无药可救的人。
后来舞会的那天晚上,许念初说的很对。
我确实是廉价的烂货没错;而这一切,都是我自己一步步向下的选择。
我知道她想拉我起来。她大概是那个地方唯一会关心我的人,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。
或许她是爱我的;可她也爱的懦弱。
不过就算我们都回到一开始,我没有选择任何人,我自爱,自尊、自持,我尽力做好该做的一切,那又能如何?
不过是另一种折磨。
没人能够解救我。
除了我自己。
(大家情人节快乐呀!)
(情人节带绿帽 一顶又一顶)
我放下琴弓,揉了揉酸胀的手腕。
视线不自觉落在手指上那一圈细细的戒指上。
金属在灯下泛着温润的光泽。当初试戴时的尺寸还正好,如今却隐隐的发紧,指根处都被勒出了一道浅浅的痕迹。
我应该没有发胖才对。毕竟在这些日子里,我几乎没怎么好好吃过饭。
所以,让我变得浮肿的罪魁祸首,大概只剩下酒精了。
可我离不开它。作为我生活中少有的慰籍,哪怕它把我的胃里烧得生疼,我还是需要那种短暂的麻痹感。
就像我离不开她一样。
我原谅她了。
可我心里很清楚——出轨这种事,只要有了第一次,就会有无数次。尤其是 Maggie 这种人,她不可能不去玩。
所以,当又一次回到宿舍发现她不在时,我的心里竟然没有什么波澜;这距离她带我去买对戒、郑重其事地许诺未来,也不过才两个星期。
无所谓了。
我从床下摸出一瓶酒,给自己倒了一杯,又取出一片止痛药。最近我几乎每天都需要吃下它,才能让自己免于疼痛的煎熬,勉强睡着。
我拨开一片药丸,刚抿了一口酒——
“这样对身体很不好的。”
声音在对面床上传来。
我回过头,Abela 坐在那里,一脸担忧地看着我。
“那个止痛药、最好不要和酒精一起吃……”她补了一句。
我眯了眯眼睛,突然意识到自己这段时间总是忽略掉她的存在。
不过她在宿舍的时间也不算多,即便在,她也一直很安静。
她和她姐姐的交流只限于必要的话;而大多数时候,只是窝在床角看书或者对着电脑,戴着头罩式耳机,把自己与外界隔开。
就像许念初一样。
我重新转过身去,把药片握在掌心。
可下一秒,手腕却被她轻轻握住。
“这样对身体不好。”
她看着我的眼睛,语气放慢,一字一句又说了一遍。
她是以为我听不懂吗?
我眨了眨眼,心里莫名觉得好笑——难道在她印象里,我的英语就这么差?
难道这么不了解我吗。我们虽然算不上很熟,却也一起住了这么久。
而且,我们其实偶尔会聊天。
我知道,她对我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在意。大概也是拜荷尔蒙所赐,毕竟我们在亲热时,从来都没有避讳过她。
她会刻意来问我一些大提琴的问题,在我产生疑问时,她又笑着说,因为感觉弦乐之间是相通的嘛。
倒也不算错。
我并不讨厌和她聊天。
不如说是很奇怪的,明明隔着一层语言的壁垒,我却很喜欢向她说很多自己的事情;因为她是会认真倾听的人。
我跟她提到老师的苛刻,是和国内截然不同的严格。我用蹩脚的英语告诉她我比赛选曲中的纠结,谈论我喜欢的作曲家,也讲练习时的瓶颈,还有手臂和肩膀始终消不掉的酸痛。
当我说起以前在国内做过针灸的事情,她瞪大了眼睛,惊讶又好奇。她问我,人类是怎么发现发现扎针可以治病的呢?我说,我也不知道。她说,她也想试试那是什么感觉。我摇头,说还是别了,很痛。
真的很疼的。
隔天,她给我带来一盒膏药。不得不说,效果确实比我之前用的都好。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。
我看着掌心里的止痛药,又抬起头,怔怔地望着她。
深蓝色的瞳孔在灯光下显得干净而清透。她脸上有着细碎的雀斑,与她姐姐如出一辙的褐色小卷发被乖乖束在脑后。
她其实长得很可爱。
我站在原地,没有说话。
不知道过了多久,她小心地拧开一瓶矿泉水,递到我手里,又递来一张纸巾。
“你哭了。”
她说。
后来,我没有喝酒,也没有吞下那片止痛药。
我只是控制不住地抽噎着,小声问她——可不可以抱我一下。
她没有拒绝。
少女的怀抱柔软而温暖,带着干净的味道,我把头歪在她的颈窝。
恰到好处的熟悉感觉,才让我发现,原来她和她一样高啊。
“我可以亲你吗?”
不知餍足的人,总会得寸进尺。
这一次,她依旧没有拒绝。
起初只是一个轻轻的吻,浅浅地落在嘴唇上。可呼吸交缠之后,一切开始慢慢失去控制。
她捧着我的脸,认真地吻着我。可就算她已经很小心,她嘴里牙套锋利的触感还是划到了我的唇瓣。
唔……
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
是久违的,被我遗忘的熟悉的感觉。
许念初在上初中的时,也戴上了这样的牙套。
那段时间我总是暗自苦恼。她接吻时笨拙又急切,总会不小心把我弄疼,可我又舍不得拒绝她难得的靠近。
可在尖利的痛感传来时,我还是下意识推开了她。
她愣愣地跪在床上,耷拉着两只湿漉漉的狗狗眼睛,一动不动地看着我。
“……是我做得不好吗?”
我的呼吸开始加快。
她第一次这样主动地向我靠近。
“不、不是……”我慌乱地解释,“只是刮的我有点疼。”
“那我们再来一次嘛。”她急切地凑过来,“再给我一次机会,好不好……”
我没有再推开她。
即使那一次,她还是不小心弄疼了我。
年少的人啊,总是轻易就被点燃。
呼吸交错,情绪失控。热烈的纠缠之间,异国的少女在一片凌乱中,狼狈地从床上爬起来。卷发早已散落在肩头,修长的手指拉开抽屉,在里面翻出一只避孕套,套在已经硬到青筋遍布的腺体上。
我熟练的帮她撸动着,看她粉红色渐渐爬上她的脸颊。
“我姐姐今晚不会回来了。”
她小心地搂着我的背,温热吐息打在我的脖颈间。
“我知道。”我轻轻地喘息着,我知道是谁。
“对不起。”她说,“她对你不好。”
我知道。我没有再把话说出口,只是默默的闭上了眼睛。
快感很快将一切都淹没。
再一次见到Maggie时,已经是第二天了。上课前一分钟,她抱着书,一个人坐到我身旁。
我跟她打了个招呼,又埋下头去看今天要讨论的文章。打印在 A4 纸上的英文字母密密麻麻,一行挨着一行。
好在,如今我已经能读懂大半,不再像刚来时那样让人头疼。
说起来,我们离开家,也已经快半年了啊。
Maggie 坐在我旁边,心不在焉地扣着手指。她的视线正落在我身上,我能感觉到。我知道她在等——等我像第一次那样失控地质问她,问她昨晚去了哪里,和谁在一起,为什么一整夜都没有回来。
可我没有。
我只是翻动纸页,假装什么都没发生。
我依然是她的女朋友。我依然爱她。就像她说她爱我那样。
虽然,我也有不想被她知道的秘密。
她仍然带我去看她的比赛,在队友面前毫不避讳地吻我。所有人都知道我是她的女朋友。她的社交软件里也只有我。
至于她的朋友们知不知道她在外面乱玩,我不确定。但可以肯定的是,我这种纵容的沉默,让她越来越肆无忌惮。
后来,她开始带我去她们圈子里的派对。
我在那些如梦似幻的夜晚里,接触到了很多人——几乎都是光鲜亮丽、家境优渥的女孩。她们的生活有无数种可能,学习只是其中最无关紧要的一项。成绩不重要,方向也不重要,家里永远有人替她们兜底,让她们一次又一次地试错。
她们的人生没有必须完成的目标。
过剩的精力无处安放——而过早见识过这个世界绚烂一面的她们,已经很难再从普通的事情里获得快乐。
于是,她们选择更热烈的方式去感受存在。
高中女生们,学着大人的样子推杯换盏,玩着无聊的酒桌游戏。暧昧而昏暗的灯光下,笑声、尖叫声、玻璃杯碰撞的脆响混和在一起,空气里全是香水、酒精和体温蒸腾后的浓郁味道。
在这里,没人把自己的感情当回事。你可以喜欢很多人,可以在同一个夜晚与不同的人接吻,可以把暧昧当成游戏,把亲密当成筹码。
只要玩得开心就好。
在这里,我跟着一个前辈学会了抽烟。
她叫什么来着?Amy,还是 Emmy?我已经记不清了。反正都差不多。
那天我们都醉得彻底。余光里,我看到 Maggie 在角落里和一个女孩接吻,灯影晃动,她的手搭在对方后颈,又渐渐往下。
于是,我转过身,靠在坐在身旁的前辈身上,抱住她,然后、主动吻了上去。
她刚抽过烟,嘴里是爆珠的甜腻香精味,混着烟草苦涩的臭味。
在过去的人生中,我一直都很讨厌烟味。
它们会附着在衣服、头发、皮肤上,根本挥之不去。就算丢进洗衣机里反复清洗,也还会若有若无地残留着。
折磨人。
而且妈妈总说,碰这些东西的,都是不叁不四的人。
但那天晚上,却莫名其妙的让我心动。
我从前辈那里讨来一支烟,笨拙地夹在指缝里。她拿出打火机,“啪”的一声,火苗猛地窜出来,我下意识一缩手。
细细的香烟掉在地上。
“你害怕吗?”她笑着弯腰捡起,熟练地点燃,深吸一口,然后缓缓开口,白色的烟雾从她的唇齿之间逃了出来。
“张嘴。”
我听话地照做。
她俯身吻上来,这次是更加直接又浓烈的尼古丁的味道,侵入我的口腔和喉咙。
“咳——咳咳——”
我弯下腰,狼狈地咳嗽,眼泪都被呛出来。
“诶呀?对不起。”她笑着拍我的背,“但这还只是一点点哟。”
好呛。
我盯着她指间那一点猩红的火光,烟头在昏暗里一明一灭。
不舒服的感觉。可我还是想试试。
最后,我只用了一晚上就学会了;并且,对它产生了依赖。
尼古丁带来的那种松弛感,强行让紧绷的神经塌陷,仿佛有人强行把我的身体按进舒适的温床。
不过那天晚上,我也确实和前辈共度了春宵。
她的床品说不上好,但也要比最差的那位温柔了不少
我晕晕乎乎的享受着她在我身后的顶弄。后来又不知道谁发现了在房间里的我们,强行托起我的下巴,和我接吻;又把她的腺体粗暴的塞入我的嘴巴里,一直顶到喉咙的最深处。
前辈似乎很大方的接受了这种行为,和别人愉快的共同享受起这个已经烂醉的Omega来。
不如说,她应该很喜欢这种多人行为;在我身后的腺体更加卖力地抽插起来。
太多刺激了,我想要一些喘息。
可是面前的Alpha根本不给我任何机会。她粗暴地拽住我的头发,强行让我把她的腺体越含越深。断断续续的窒息感让我的眼前一片模糊,身下的快感也被无限放大。
不得不说,我其实很喜欢这样。
不过我大概看起来很狼狈吧,衣服被褪去了大半,两个乳房就这样袒露在空气中,随着动作摇晃着。
简直像一件专供Alpha的发泄玩具一样。
意识浮浮沉沉。这是哪里?只留下远处的一盏小灯,让我看不清任何东西。我独自一人狼狈地蜷缩在床上,脸上、身上似乎都还沾着别人污秽的液体。
门虚掩着,外面的音乐声隔着墙传进来,低沉而模糊,像从水底传来的响动。
我有一瞬间恍惚——
如果被她看到我这个样子,她会生气吗?
这个念头在脑海里转了一圈,沉下去;又浮上来。
如果被她看到我这个样子,她会生气吗?
还是……她根本不会在意。
视线失焦,我盯着天花板上旋转的光影。身体和灵魂像被拆开来,各自漂浮着。我忽然生出一种荒谬的感觉——仿佛自己是一件已经死去、但仍然残留一点温度的物件。
啊,就这样让我死去吧。
像一只被拆坏的旧玩具,被开膛破肚,里面填充的棉絮散落一地。没有谁会认真去修补,也没有谁会为它的破损感到惋惜。
我是无药可救的人。
后来舞会的那天晚上,许念初说的很对。
我确实是廉价的烂货没错;而这一切,都是我自己一步步向下的选择。
我知道她想拉我起来。她大概是那个地方唯一会关心我的人,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。
或许她是爱我的;可她也爱的懦弱。
不过就算我们都回到一开始,我没有选择任何人,我自爱,自尊、自持,我尽力做好该做的一切,那又能如何?
不过是另一种折磨。
没人能够解救我。
除了我自己。
(大家情人节快乐呀!)
(情人节带绿帽 一顶又一顶)